诺姆·乔姆斯基
| 本条目需要編修,以確保文法、用詞、语气、格式、標點等使用恰当。(2015年4月6日) |
body.skin-minerva .mw-parser-output table.infobox caption{text-align:center}
| 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 | |
|---|---|
 2015年的乔姆斯基 | |
| 出生 |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 Avram Noam Chomsky (1928-12-07) 1928年12月7日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
| 母校 | 宾夕法尼亚大学(1949届文学士;1951届文学硕士;1955届哲学博士) |
| 配偶 |
|
| 网站 | chomsky.info |
科学生涯 | |
| 研究領域 | 语言学、分析哲学、认知科学、政治评论 |
| 机构 |
|
| 论文 | 转换分析(1955年) |
| 签名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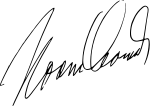 | |
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英语:Avram Noam Chomsky,1928年12月7日-),或译作“荷姆斯基”,美国哲学家、语言学家、认识学家、逻辑学家、政治评论家。乔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他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对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他對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所著《口語行为》的評論,帮助发动了心理学的认知革命,并挑战了1950年代研究人類行為和语言方式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为主义。他所採用以自然為本來研究语言的方法也大大地影響了语言和心智的哲学研究。他的另一大成就是建立了乔姆斯基层级:根据文法生成力不同而对形式语言进行的分类。乔姆斯基还因他的政治热忱而著名,尤其是他对美国和其它国家政府的批评。從1960年評論越南戰爭以來,他的媒體和政治評論便越來越著名。一般认为他是活跃在美国政坛左派的主要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把自己归为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并且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同情者。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说,在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是被文献引用数最多的健在学者,并是有史以来被引用数第八多的學者。
目录
1 生平
2 对语言学的贡献
2.1 爭議
3 对心理学的贡献
4 对反科学文化的批评
5 在其它领域的影响
6 政治观点
7 乔姆斯基论恐怖主义
8 对美国政府的批评
9 支持各國反對運動
10 参见
11 参考文献
12 外部連結
生平
乔姆斯基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他的父亲威廉·乔姆斯基(William Chomsky)是一位希伯来学者,来自一个后来被纳粹灭绝了的乌克兰小镇。他的母亲艾尔西·乔姆斯基·西蒙诺夫斯基(Elsie Chomsky Simonofsky)是白俄罗斯人,但跟她的丈夫不同的是,她生长在美国,说「普通的纽约英语」。他们两人的第一语言都是意第绪语,虽然乔姆斯基本人说父母在家禁止讲这种语言。他说,他们住在分裂为「意第绪区」和「希伯来区」的犹太人聚居地,他的家庭认同后者,并用「纯粹的希伯来文化和文学」教导他。
乔姆斯基记得他的第一篇文章写於十岁那年,文章是论在巴塞罗那陷落之后,纳粹主义蔓延的威胁。从十二岁或十三岁开始,乔姆斯基更加彻底地认同无政府主义。
他毕业於费城中央高中,从1945年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师从哲学家C·维斯特·切奇曼(C. West Churchman)、尼尔遜·古德曼(Nelson Goodman)和语言学家泽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学习哲学和语言学。哈里斯对他讲授了自己在语言结构线性算子方面的发现。乔姆斯基后来把这些解释为对来自标记系统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产物的操作。哈里斯的政治观点对乔姆斯基政治立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9年,乔姆斯基和语言学家卡罗爾·沙茨结婚(Carol Schatz)。婚后育有两个女儿分別是阿维瓦(Aviva,1957年)與戴安(Diane,1960年),和一个儿子哈里(Harry,1967年)。
乔姆斯基于1955年从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他的大部分博士研究是用四年时间以哈佛大學年轻学者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在博士论文中,他开始发现自己的一些语言学思想;后来他将这些进一步阐发,写成了他在语言学方面大概最有名的著作《句法结构》。
乔姆斯基于1955年开始执教於麻省理工学院,1961年成为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系(现在的语言学与哲学系)的正教授。1966到1976年间,他担任现代语言和语言学的法拉利·P·沃德(Ferrari P. Ward)教席。1976年他被任命为学院教授,之后至近五十年来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教课。
正是在此期间,乔姆斯基开始公开地参与政治。当他在1967年在《纽约书评》上发表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责任〉[1]后,乔姆斯基成为越战主要反对者之一。从那时起,乔姆斯基便因他的政治立场而出名,对世界各地的政局发表评论,并撰写了大量著作。他对美国外交政策及美国权力合法性的批判影响深远,并因而成为富有争议的人物。他有左派的忠诚追随者,但也受到右派及自由派越来越多的批评,尤其是针对他对911事件的反应。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给乔姆斯基带来了人身威胁。他的名字被列在泰德·卡辛斯基(Theodore Kaczynski,「邮箱炸弹杀手」)的预定名单上。在卡辛斯基被捕以前,乔姆斯基让人检查收到的邮件以防炸弹。他自称也经常被警察保护,特别是在麻省理工校园的时候,虽然他原则上不同意这种保护[2]。
尽管对美国百般批评,乔姆斯基还是生活在美国,他的解释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3]。后来他又阐发为:「国与国之间的综合比较没有什么意义,我也不会这么比较。不过美国有些成就,特别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几个世纪来争得的领先地位,是值得敬仰的。」[4]。
对语言学的贡献
《句法结构》是乔姆斯基介绍转换生成语法的《语言学理论的逻辑结构》一书的精华版。这一理论认为说话的方式(词序)遵循一定的句法,这种句法是以形式的语法为特征的,具体而言就是一种不受语境影响并带有转换生成规则的语法。儿童被假定为天生具有适用于所有人类语言的基本语法结构的知识。这种与生俱来的知识通常被称作普遍语法。
爭議
乔姆斯基的一些語言學學說一直飽受爭議。例如他聲稱“只要掌握一種語言的語法,便已經俱備該語言的語言學競爭力”,暗示學習語言並不需要學習該語言的背景文化。此論點被包括西門菲沙大學語言學教授沙潘斯基 (Nathalie Schapansky)在內的一些社會語言學家公開反對及批評。此外,關於普遍語法以及X-Bar語法的論述也一直爭議不斷:出於普遍語法的假設,應用X-Bar語法時不得不假設很多空白詞類(empty categories)。例如:法語和英語在很多情況下都需要用補語指示詞(Complimentiser)引出從句,而粵語卻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補語指示詞,但是將X-Bar理論應用於粵語時,使用者不得不假設粵語有“空白補語指示詞”(unpronounced/empty complimentisers)。
对心理学的贡献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著作,对于心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普遍语法理论被很多人认为是对既定的行为主义理论的直接挑战。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儿童如何习得语言以及什么是真正理解语言的能力都有深远的意义。乔姆斯基理论的很多基本原则现在已经在某些圈子裡被普遍接受。1959年乔姆斯基出版了对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口語行为》一书的长篇评论。斯金纳在他的书里试图用行为学理论解释语言问题,他将「口語行为」定义为一种从他人那里学习得来的行为,这就超出了语言学家通常关注的范围而对交往行为提出了普遍解释。
斯金纳的研究方式与传统语言学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它关注语言使用的情境,比如他认为跟人要水,与把一样东西称为水,与回应他人要水的请求在功能上是不同的。这种因功能而异的回应方式需要单独进行解释,这就与传统的语言观以及乔姆斯基的心理语言学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关注的是词语的精神表象,并假定某个词一旦被学会就会以各种功能出现。乔姆斯基1959年对斯金纳的批判虽然也涉及不同口头行为的功能,但主要集中在对斯金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行为心理学的批判。乔姆斯基论文的主要观点是,将动物研究中的行为原则应用到实验室之外的人类身上是毫无意义的, 要想理解人类的复杂行为,我们必须假定负有终极责任的大脑中有一些无法被观测到的实体。这两点都与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针锋相对。应该注意到,乔姆斯基1959年的这篇论文也曾受到严厉的批判,其中最有名的一篇是肯尼斯·麦克考科戴尔1970年发表在《行為的實驗性分析期刊》(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volume 13, pages 83-99)上的《论乔姆斯基对斯金纳〈口語行為〉的评论》。这篇论文和其它类似的评论都指出一些为外行忽略的事实:比如乔姆斯基不管是对行为心理学还是对斯金纳的激进行为主义都并不真正了解,而且犯了很多令人难堪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乔姆斯基的论文并未完成它所宣称的任务。那些深受这篇论文影响的人,要么是从来就与他观点一致,要么从来没读过这篇文章。
通常认为乔姆斯基对斯金纳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设的批评开创了美国心理学从1950年代到70年代的「认知革命」,也就是从以行为研究为主转变为认知研究为主。乔姆斯基在他1966年的《笛卡尔主义语言学》和后来的著作中对人类语言能力作出的解释后来成为心理学某些领域的研究范本。现在很多关于头脑如何运作的观念都是从乔姆斯基富有说服力的思想中发展而来的。有三个基本思想。首先,头脑是「认知的」,或者说头脑中包含精神状况、看法、疑惑等等。先前的观念甚至不承认这一点,认为只存在「如果你问我想不想要X,我会回答是的」这样的逻辑关系。而乔姆斯基则相信通常的看法一定是正确的,即头脑中包含看法甚至无意识的精神状态。其次,乔姆斯基认为成年人的大部分智力活动都是“先天的”。尽管儿童并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某种语言,所有儿童都天生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这种能力使他们得以在最初几年中很快吸收几种语言。后来的心理学家将这一论断广泛应用于语言问题之外。最后,乔姆斯基将“模块化”作为头脑认知结构的关键特征。他认为头脑是由一系列相互作用各司其职的亚系统组成的,彼此间进行有限的交流。
对反科学文化的批评
乔姆斯基对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科学的批判持有强烈异议。
「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用我所知道的方法,那些被指责为“科学”、“理性”和“逻辑”的方法研究此类问题。因此当我读那些论文(按:此处应指后现代或后结构的论文)时,我指望他们能帮我超越这种局限,或指出一个全新的方向。我恐怕是失望了。我承认这也许是我的局限性。通常我读到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那些多音节术语的时候,只是匆匆扫过。我能理解的多半是老生常谈或明显的谬误,然而那些只在所有词语中占一小部分。确实,有很多其它东西我也不懂,比如最新的物理学和数学期刊上的文章。但是不一样。后一种情况下,我知道如何去理解他们,在我格外感兴趣的时候也那样做过;而且我知道那些领域的人能够根据我的水平向我解释,让我弄懂我感兴趣的部分内容。相反,好像没有人能跟我解释最新的“後”什麼之類的理論。除了老生常谈,胡言乱语和明显的错误外还有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去理解。」
乔姆斯基注意到,对「白人男性科学」的批判类似於反犹主义及「德意志物理学」运动期间,纳粹出于诋毁犹太科学家的研究的政治目的对“犹太物理学”的攻击。
「事实上,「白人男性科学」的整套说法都让我想起「犹太物理学」。也许这是我的另一个不足之处,但是我读一篇科学论文的时候无法判断作者是否白人或者男性。对课堂上、办公室或其它地方的讨论也是如此。我着实怀疑那些与我共事的非男性、非白人学生、朋友和同事会乐于接受这种说法,承认他们的思维和理解方式由于“性别与种族的文化”而与“白人男性科学”有所不同。我估计他们对此的反应不仅仅是“惊讶”。」
在其它领域的影响
乔姆斯基的模式也被当做其他一些领域的理论基础。计算机科学的基础课程中会涉及乔姆斯基体系,因为它传达了对多种正规语言的洞见。这一体系也可以从数学的角度来讨论,并引起了数学家,尤其是组合数学家的兴趣。很多演化心理學的论点也是由乔姆斯基的研究结果中引发的。
1984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尼尔斯·吉尔内用乔姆斯基的生成模式解释人类免疫系统,他把「蛋白质结构的各种特征」类比为「生成语法的各个组成部分」。吉尔内的斯德哥尔摩诺贝尔讲座就题名为「免疫系统的生成语法」。
政治观点
乔姆斯基於1970年代曾經支持紅色高棉,並否認其大屠殺暴行。[5][6]
乔姆斯基是美国激进派政治人物的最著名代表之一。他自称无政府主义者,按照他的说法也就是挑战并试图消除一切不正当的等级制度。他尤其认同无政府主义中以劳工为核心的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很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乔姆斯基并不完全排斥选举政治;他对美国大选的立场就是:公民应为当地民主党投票以防止共和党上台,而在共和党没有希望获胜的地区则应该支持更加激进的候选人比如绿党。他自称为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同路人」,以示与纯粹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并以此解释他为何有时愿意国家机器介入。
乔姆斯基认为自己是经典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他甚至还自称犹太复国主义者,尽管他意识到他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在今天已经被很多人认为是反犹太复国主义。总体来说,乔姆斯基对传统的政治称谓和分类都不感兴趣,他宁可让他的观点本身说明问题。他主要的政治活动方式是为杂志撰文、写专著及发表演说。他也是政策研究学院的高级学者。
《现代美国哲学家辞典》将乔姆斯基称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左派批评者中最有影响的人之一」。
乔姆斯基论恐怖主义
针对美国在1981年和2001年宣布的反恐战争,乔姆斯基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源头是美国领导的世界强国。他引用一部美国军事辞典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说那是:“故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以策动恐惧,试图强迫或恐吓政府或社会以追求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目标。”他据此指出,恐怖主义是对某种行为的客观描述,不论行动者是否為国家机器。就美国入侵阿富汗,他说:「肆意杀害无辜平民是恐怖主义而非反恐战争。」论恐怖主义的效力:「首先,恐怖主义确实有效,不会失败。它是有效的。暴力总是有效,世界历史一向如此。其次,通常所谓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这一说法是极大的分析失误。与其他暴力手段一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是强者的武器。恐怖主义被称作弱者的武器,是因为:强者同时控制着言论,他们的恐怖行径也就可以不算。这是普遍情况。我几乎想不出历史上有任何反例,甚至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也这么看。比如说纳粹,他们没有在欧洲占领地实行恐怖主义,他们是保护当地居民免受游击队的恐怖袭击。正如其它抵抗运动一样,当中存在恐怖主义。纳粹是在反恐怖。」[7]
至于对恐怖主义是应当谴责还是支持,乔姆斯基认为,恐怖主义(及暴力和强权)总的来说应受谴责,除非在某些情况下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恐怖(或暴力及滥用强权)。在1967年一场关于政治暴力的合法性的辩论中,乔姆斯基主张,越南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是不正当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讲,在某些情况下那些活动又是有理由的:
「我不认为由于民族解放阵线的恐怖活动令人发指,就应该对之一味谴责。虽然这可能听上去很邪恶,但我们实在应当把代价作个比较。如果我们要站在道德立场上看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如此—我们就要问一问:使用和不使用恐怖活动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不使用恐怖活动的后果就是让越南的农民继续过着菲律宾农民那样的生活,那我想恐怖活动是有合法性的。但是,正如我先前所说,我不认为成功是通过恐怖活动取得的。」[8]
乔姆斯基认为,那些美国政府进行的被他称为恐怖主义的活动都禁不住这样的检验。对美国政策的谴责是他的著作的要点之一。
2013年9月,喬姆斯基接受今日俄羅斯訪問,以曼德拉和海珊為例說明,美國的「恐怖份子清單」是根據政治需要來決定誰該列入或移出,是不受監督的作法。喬姆斯基說:「歐巴馬寧可錯殺一百的『全球暗殺政策』(global assassination campaign),倒退到8百年前13世紀的人權水平。」[9]
对美国政府的批评
乔姆斯基对美国政府一贯持鲜明的批判立场,而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成为他的很多政论的基点之一。乔姆斯基对此提出两点理由:首先,他相信,如果他的著作是针对自己国家的政府,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其次,他认为,美国作为世界上现存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以前的所有超级大国一样霸道。
喬姆斯基說,他希望有生之年能見到小布希和歐巴馬等人被逮捕並移送國際刑事法庭,但他知道這不可能實現,因為:美國通過一項法律,授權總統派軍行使武力救回任何被移送國際刑事法庭的美國人。
支持各國反對運動
2013年,土耳其抗議運動支持者,至麻省理工邀請喬姆斯基聲援。喬姆斯基同樣舉起I'm also a çapulcu,聲援土耳其反對派。
参见
- 宁姆
参考文献
^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 "The Cutting Edge of the Political Left", March 13, 2006 The Hour CBC
^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 Bill Bennett", May 30, 2002 American Morning with Paula Zahn CNN
^ "Question time", November 30, 2003 The Observer
^ 沈旭暉. 解構中國夢: 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15: 190. ISBN 9789629966423.
^ 毓民特區:頭腦發熱 言論反動-黃毓民 立法會議員. 2015-04-07.
^ Noam Chomsky. The New War Against Terror. chomsky.info // Delivered at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October 18, 2001 [2013-09-14].
^ The Legitimacy of Violence as a Political Act?, Noam Chomsky debates with Hannah Arendt, Susan Sontag, et al.
^ 台灣立報 2013-02-08 :海珊與曼德拉 互联网档案馆的存檔,存档日期2013-12-10.
外部連結
- 諾姆·喬姆斯基官方網站
- 喬姆斯基:論語言與文化
| ||||||||||||||||||||||||||||||||||||||||||||||||||||||||||||||||||||||||||||||||||||||||||||||||||||||||||||||
| ||||||||||||||||||||||||||||||||||||||||||||||||||||||||||||||||||||||||||||||
| ||||||||||||||||||||||||||||||||||||||||||||||||||||||||||||||||||||||||||||||||||||||||||||||||
|

Comments
Post a Comment